歷史學家李劍鳴認為?對此,著名歷史學家李劍鳴教授有過清晰的說明:“在選取研究方向和確立課題方案的過程中,就本課題做一番學術史的梳理,就成了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李劍鳴教授的觀點完全正確,值得重視。那么,歷史學家李劍鳴認為?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古代沒有民族英雄概念
“民族”的概念確實近代以來才進入中國,這個理由看似有理,卻事實上混淆了概念和概念的內涵。概念可以后起,但之前的事物只要滿足概念內涵,我們就可以說它屬于此概念。
我們可以在現代歷史學中找到大量的例子: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是“部落聯盟首領”,但當時顯然沒有“部落聯盟首領”這個概念本身;古代郡縣制下形成了“官僚體制”,但“官僚體制”也不是古代概念……可以說,歷史學中學術化語言描述和分析所使用的,都不是古代就有的概念,怎么到了岳飛的“民族英雄”這里就出了問題呢?執此論者的證據稱“(民族一詞)在19世紀文獻中極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開始出現井噴之勢”,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假如去檢索“人類”這個詞,也會是19世紀之后“才開始出現井噴之勢”,難道就能說明19世紀前的古人就不屬于“人類”了么?
岳飛是“民族英雄”是歷史學的結論
分析性和理論性取代敘事性,成為史學的主要特色,描述性史學變成了分析性史學。如果說,“舊史學”解釋過去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宗教、道德和政治領域,那么現代史家則越來越倚重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概念工具,諸如結構、趨勢、模式、變遷、階級、種族、文化、性別這樣的術語,頻繁出現于一般史學論著當中。
回顧歷史:我們究竟應該以何種標準給“民族英雄”下定義?官方的,學術的,還是順乎民意的?民族英雄和正義與邪惡的關系是什么?這些問題恐怕尚需各方面專家做出回答。
百度百科:民族英雄是指維護國家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完整,保障國家安全,維護人民利益及民族尊嚴,在歷次反侵略戰爭中,獻出寶貴生命和作出杰出貢獻的仁人志士。近代的民族英雄主要是指在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中法戰爭、抗擊八國聯軍、中俄戰爭、抗日戰爭中作出重大犧牲的國家棟梁和民族精英。
近日,有消息說教育部教學大綱規定以后不再把岳飛當作民族英雄,這引起了人們的強烈爭論。普遍的看法是,把岳飛這些民族英雄的桂冠摘去,將很大程度上引起教育斷層、歷史生態的危機。批評者進而對此舉究竟在多大意義上促進民族團結懷有疑問。
雖然后來又有消息說,一切都是謠言。但這并不意味著岳飛的民族英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事實上,岳飛的問題始終是歷史學家的公案之一。而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與所謂的將大屠殺紀念館改為和平紀念館的功利性歷史觀頗有牽連,因此,關注就并非不必要。
岳飛簡歷:(1103—1142年)字鵬舉,河南安陽人,南宋杰出的軍事家、戰略家,民族英雄[1-3],抗金名將。他精通韜略,也精于騎射,并長于詩詞、書法,其高尚品格和愛國主義精神為歷代的人民所傳誦。
論文寫作,是一項觸手紛綸的學術工程。從積學儲寶,到辨章學術;從深造有得,到著述立說,不但曠日廢時,而且千頭萬緒。平素,講究治學工夫;臨筆,提煉核心論旨,則如順水推舟,容易勝任愉快。草擬大綱,好比航道規劃,路徑指引,未下筆之前,只是學術研究的大方向。必須反復論證,持續推敲。一旦發現偏差出入,就當毅然決然修正與調整。闡說如下:
一、 治學工夫與核心論旨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中庸》提示為學五大工夫。可作草擬大綱、撰寫論文的準則和門徑。專心投入,用心思考,是研習知識,寫作論文的必要態度,關系研習成效,寫作的優劣。孔子曾言“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學與思必須相輔相成,兼顧并重。《禮記·中庸》曾提示為學之工夫,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朱熹于《白鹿洞書院學規》加以凸顯呼應,《四書集注》《朱子語類》中,亦多所闡釋發明,堪稱研習知識之指標,讀書治學之金針,可以度己度人,作為奉行的綱領與津筏。今借用《中庸》所提示,經轉化應用,連結到草擬大綱和論文撰寫上,亦怡然理順,堪作遵行的準則,和循序漸進的指南。
為什么要撰寫論文?就研習知識來說,是為了發表成果,分享心得。心得識見若未經條理化表述,未經系統化勾勒,未經邏輯化提出,將可能只是吉光片羽,一鱗半爪,存留于內心深處而已。

一、注重更新知識,增強科研意識
歷史科目包括內容特別廣泛,一定時期的歷史就是一定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綜合。因此,歷史工作者應多讀書,要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懂地理”。比如讀一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思想理論著作、文化常識方面的書籍,尤其是歷史方面的專業書籍(如《左傳》《戰國策》,《資治通鑒》甚至全部《二十四史》)。要想具有廣泛的知識面,就需要繼續學習,不斷給自己充電。現代社會強調終生學習觀,尤其作為歷史工作者,就更應該有一個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科學、人文素養。由于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歷史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因此歷史工作者的知識要不斷更新,不斷注意汲取專業知識的營養,做到與時俱進。同時注意跨學科知識的學習,做到旁敲側擊,觸類旁通,要求加強歷史、政治和地理的學科交叉,才能形成知識的綜合和遷移能力,也才能在備課中見微知著,講課中深入淺出,才能不斷啟迪心智,培養創造思維。
除此之外,歷史工作者在新課改過程中還要不斷增強科研意識,及時把握當今史學發展動態和了解史學的新成果,同時能把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吸收到歷史研究中去,深化自己的歷史知識和歷史理論水平,不斷強化自己的創新能力,在培養歷史思維能力方面有所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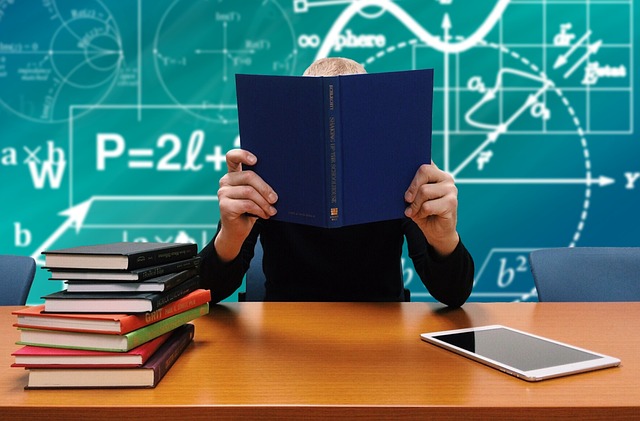
1.《隔岸觀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2. 《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3.《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1月。
4.《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2002年作為《美國通史》第1卷重印;2006年收入“中國文庫”。
5.《文化的邊疆: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文化關系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
6.《偉大的歷險:西奧多·羅斯福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5月。
7. 《大轉折的年代: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1、 《美國歷史上的社會運動與政府改革》(張友倫、李劍鳴主編),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2月。
2、《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就職演說全集》(李劍鳴、章彤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最新修訂版,1997年7月。
3、《20世紀美國和加拿大社會發展研究》(李劍鳴、楊令俠主編),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4、《美國歷史的多重面相:慶賀歷史學家張友倫教授八十華誕論文集》(李劍鳴、楊令俠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
5、《世界歷史上的民主與民主化》,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1月。
以上就是歷史學家李劍鳴認為的全部內容,其次,歷史學家在研究過程中還要確立正確的歷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與運用固然重要,但是歷史研究者也要意識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個臺階,以達到認識歷史的目的。對歷史的認識不僅在于認識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