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滿族經(jīng)典民歌100首 對滿族音樂的認(rèn)識 好聽的滿族歌曲 滿族民間音樂有哪些 滿族的音樂特點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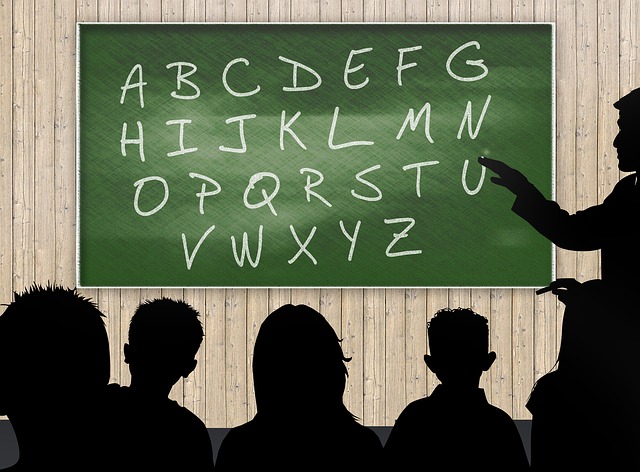
滿族民歌內(nèi)容豐富,較之漢族民歌,多了一些漁、獵穗梁辯、牧勞動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親人內(nèi)容歌曲。其歌詞語言通俗、活潑,其旋律質(zhì)樸、簡明。農(nóng)村中的滿族民歌這一特征更為明顯。滿族日常生活中離不開歌唱,活潑動情的小唱幾乎涉及到滿族整個人生禮俗,唱出了他們猜缺的愿望和心聲。自降生聽《悠搖車》,稍大一些學(xué)唱《小板凳》、《河河沿》,童年的《抓嘎拉哈歌》,少年的放牧山歌,青年的情歌、結(jié)婚的喜歌,出征的戰(zhàn)歌,圍獵的獵歌,以及豐收喜慶,歲時節(jié)日,祝福賀壽,凱旋慶功,悲歡離合都有歌,其音樂風(fēng)格多彩多姿,但基調(diào)豪放,朗爽,即使表現(xiàn)哀婉情緒的音樂,也不失其剛健強勁的內(nèi)質(zhì)。
滿族民歌有搖籃曲、兒歌、情歌、勞動歌、風(fēng)俗歌、山歌、小調(diào)、喜歌、戰(zhàn)歌、敘事歌等等,形式多樣,內(nèi)容幾乎包括其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其音樂也各有特色。 在關(guān)東廣大農(nóng)村流傳著豐富多彩的反映滿族人民勞動、祭祀、游戲、出征和日常生活的民歌、兒歌。其中有漁民號子《跑南海》、山歌《開山調(diào)》、牧歌《溜響鞭》、《渣賣喜歌》等;反映愛情的有《伊勒哈穆克》、《紅絨線》、《煙荷包》、《十二月》等;游戲歌有《抓嘎拉哈》、《拍手歌》;反映出征內(nèi)容的有《出征歌》、《八角鼓咚咚》;反映婦女生活的《丹查拉米》、《酸棗顆棵》;兒歌有《干草垛插金刀》、《風(fēng)來咯》等。

滿族主要分布在中國的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以遼寧省最多。滿族人口在中國55個少數(shù)民族中僅次于壯族居第二位。主要從事農(nóng)業(yè),兼營漁牧業(yè)。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但現(xiàn)在只有黑龍江省愛琿鎮(zhèn)和富裕縣,還有少數(shù)老年人會說滿語,其他地方絕大多數(shù)滿族人民已通用漢語。
滿族傳統(tǒng)音樂由民間音樂、薩滿音樂和宮咐首廷音樂構(gòu)成。其民間音樂包括民歌、說唱音樂、器樂、歌舞音樂和戲曲音樂。民歌常見有勞動號子、“夸山調(diào)”(山歌)、“咧咧”(小唱)等,活潑動情的小唱幾乎涉及到滿族整個人生禮俗。18世紀(jì)中期,“八旗子弟”創(chuàng)作了一種新的鼓詞,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為“清音子弟書”。
普天下的《搖籃曲衡塵數(shù)》都是這般靜謐恬美,簡單明了隨口哼唱的歌詞,配襯上祖輩流傳下來的悠揚曲調(diào),在溫柔女聲“把卜著”的傾訴和兄槐呢喃中,我們仿佛重回母親的懷抱,重回嬰孩本真時代的心兒也漸漸融化。
渤海國亡后,遼統(tǒng)治者唯恐其作亂,將渤海族人分散強遷至各地,到了金代,遼東地區(qū)的渤海族人逐漸增多,“人口達(dá)到五千余戶,兵士有三萬人”,① 金統(tǒng)治者也恐其難控制,故逐年將其遷徙到山東防衛(wèi),每年有數(shù)百戶,“到熙宗皇統(tǒng)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將渤海人大批遷徙到中原地區(qū)”,② 如此大批渤海人遷徙中原,必將渤海音樂文化帶到中原,繼續(xù)流傳,最后以融入漢族音樂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隱性發(fā)展,正如《金史·樂志》載:“……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zhuǎn)化的歷史階段,具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的漢文化從經(jīng)濟生活、政治體制、思想意識、倫理道德、風(fēng)俗習(xí)慣對女真族都有較大影響。金統(tǒng)治者主張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漢人都是國人;主張學(xué)習(xí)漢語和漢儒的經(jīng)書和理學(xué)等著作,拜漢儒為師(如金熙宗請宋人韓枋為師,海陵王完顏亮及其兄、子曾請漢儒張用直為師)。在漢文化影響下,金代的文字“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合本國語,制女直(女真)字”;③ 宗教改信佛教和道教;其繪畫、雕塑、建筑發(fā)展很快,皆似漢風(fēng);自然科學(xué)方面的天文、數(shù)學(xué)、醫(yī)學(xué)等都有較大發(fā)展。在文學(xué)方面,女真文人在創(chuàng)作上跨越了漢文化的楚辭、漢賦階段,“金一代的詩人,一開始就是從唐詩、宋詞著手。女真文學(xué)的形式主要是詩、詞、曲、散文、戲劇等。”④ 金代興起的“院本”和余好“雜劇”,為傳入中原的女真族音樂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領(lǐng)域,其中“院本”運用了大量女真族音樂,據(jù)專家、學(xué)者考察:“在690本‘金院本’中,采用漢人古樂曲的只有16本,其余可能運用女真音樂或金代北方民族音樂。”① 此后,在“金院本”和“諸宮調(diào)”基礎(chǔ)上形成的“??音樂。如元代著名女真族戲劇家李直夫創(chuàng)作的雜劇《虎頭牌》,“……尤其是對女真人風(fēng)俗和軍俗的描寫,具體而生動,演出時《虎頭牌》采用了〈阿那忽〉、〈風(fēng)流體〉、〈唐兀歹〉、〈也不羅〉等女真樂曲。”②《虎頭牌》“劇本第二折用了許多源出于女真音樂的北曲,元明間這一折頗為流行,由于用17個曲牌組成套曲,通名‘十七換頭’”。③在元明間的戲劇中,賈仲明創(chuàng)作的《金安壽》和關(guān)漢卿創(chuàng)作的《南呂第一枝》的唱詞中,曾提到的“者刺古”、“鷓鴣”、“垂手”都是女真族的樂舞名稱,當(dāng)女真音樂以其簡約的民歌形虛毀氏態(tài)進入中原時,正值漢文化的戲劇發(fā)端時期,在此良機,女真族音樂從民歌躍入說唱和戲曲,進入了一個幸運的“時空”。以后又和其他北方民族音樂一起形成了日后較有影響的“北曲”。《中國音樂詞典》“北曲”詞條云:“(北曲)其中有唐、宋以來的歌舞大曲,宋、金以來的說唱諸宮調(diào),宋代流行的詞調(diào),以及鼓子詞、轉(zhuǎn)踏、唱賺等說唱音樂或歌舞音樂,還有少數(shù)民族的民歌,尤其女真族的民歌占有相當(dāng)比重。”另外,女真族的“臻篷篷歌”和太平鼓也傳入中原,“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④ 至明朝“京師有太平鼓之戲”,而且“有結(jié)為太平鼓會者,聚眾數(shù)百人。”⑤
清入關(guān)后,統(tǒng)治者一方面為治理國家鞏固差散政權(quán)積極竭力學(xué)習(xí)漢族文化;另一方面為維護滿族“國語騎射”的民族意識又制定了一些方針措施。由此,形成滿文化自身不斷發(fā)展的同時,又逐漸融入漢文化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八旗子弟樂”的出現(xiàn),以及“八旗子弟樂”中的子弟書、牌子曲、高蹺、太平鼓、和經(jīng)過“八旗子弟樂”化的什不閑、太平歌、道情等音樂與其后中原的京韻大鼓、梅花大鼓、單弦牌子曲,東北的滿族大鼓、二人轉(zhuǎn)等音樂的淵源關(guān)系、都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出滿文化特征。正如李家林在《關(guān)于〈北平俗曲略〉的話》一文的第一部分“北平俗曲的來源”中所說:“我們研究北平俗曲的結(jié)果,知道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從外省輸入的。……東北由遼金清輸入打連廂、倒喇、群曲、蹦蹦戲等;……傳播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諸族為主,……”
清統(tǒng)治者為鞏固政權(quán),將滿族諸部編成八旗分散居住在全國各地,由此滿族的民間音樂也被帶到全國各地,流傳在駐守邊疆八旗軍中的“八旗子弟樂”,便是在滿族民歌和薩滿神歌的曲調(diào)上,填以具有簡單故事情節(jié)的歌詞,用八角鼓伴奏,來抒發(fā)心中思鄉(xiāng)之情的音樂。這種長于抒情、敘事一唱到底的音樂形式傳入京都后,受到人們喜愛,八旗文人便參照民間鼓曲的格式和北方音韻的“十三道大轍”,創(chuàng)作出近似鼓曲的“八旗子弟書”,后因初創(chuàng)地域和風(fēng)格不同,又分成“高亢紅火、慷慨激昂”的“東城調(diào)”和“纏綿悱惻、婉轉(zhuǎn)低回”的“西城調(diào)”。最初“八旗子弟書”用滿語寫作演唱,在逐漸混入漢語演唱時稱為“滿漢兼”;其后根據(jù)聽眾的需要,又有一部分滿漢文對照的唱本,或用滿語或用漢語演唱,謂之“滿漢和壁”;最后因滿族通用漢語,故“子弟書”也都用漢語寫作和演唱了。在此期間,“子弟書”傳到天津,形成“語言通俗流暢,接近方言口語,節(jié)奏較快”的“天津子弟書”(也稱“衛(wèi)子弟”);后又傳到盛京(沈陽)稱為“清音子弟書”。① 清末。“子弟書”衰落。在其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了流行于京津一帶的“梅花大鼓”,以及與“木板大鼓”相結(jié)合的“京韻大鼓”。②
在東北滿族人民中,還流傳著一種手執(zhí)八角鼓自編自唱的藝術(shù)形式,名為“八角鼓”。清入關(guān)后,它已具有說唱特征雛形,也傳入關(guān)內(nèi)。此后,“八角鼓”的表演形式以滿文化特征和其他滿族音樂文化因素,以及中原音樂文化一起促成“單弦牌子曲”的形成和發(fā)展。“單弦牌子曲”運用滿族樂器八角鼓伴奏;其音樂吸收“子弟書”中的“西城調(diào)”① 和明、清流行的時調(diào)小曲(其中有可能包括滿族民歌和滿族八角鼓音樂),以及因滿族士兵寶恒(又名小岔)唱得最好而命名的“岔曲”。在其表演形式從群唱改變成“單弦”形式,以及文學(xué)、音樂內(nèi)容又進一步充實提高時,滿族單弦表演藝術(shù)家德壽山等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滿漢文化,此后,“單弦牌子曲”盛傳不衰至今。此外,滿族八角鼓也對其他地區(qū)的說唱藝術(shù)有一定的影響,“現(xiàn)在山東流行的聊城八角鼓與滿族八角鼓有淵源關(guān)系,河南大調(diào)曲子、蘭州鼓子、青海平弦等都吸收過八角鼓的曲牌。”②
上述表明,族及其先世的音樂在進入中原后,伴隨著漢族音樂的進化,也處在一個有利于自身發(fā)展的良好氛圍中,它在不斷發(fā)展中與漢族音樂相融合。事實證明,北方中原的民間音樂的旋律舒展流暢、節(jié)奏清晰歡快、性格陽剛爽直等特點的形成,無不受著北方各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其中也包括滿族音樂文化)的影響。 東北地區(qū)是滿族(女真族)的發(fā)源地,從金帝國至清帝國,無論是入主中原的貴族還是留居?xùn)|北的貴族,都明顯大量地吸收漢文化,這從史料記載和出土文物中可以明見。但在民間,滿族(女真族)風(fēng)俗文化對漢族的影響,勝于漢族生產(chǎn)技術(shù)對滿族的影響。
金代,統(tǒng)治者從關(guān)內(nèi)虜遷大批漢人到東北,這些遷徙到東北的漢人,不少都成為女真人的奴婢,形成金代奴婢戶大都是漢人。金統(tǒng)治者強迫東北地區(qū)漢人女真化,曾下令“禁民(漢人)漢服及削發(fā)不如式者死,”③ 由此,“女真人統(tǒng)治下的漢人在服式、發(fā)式、居住、飲食方面都已相當(dāng)程度的女真化。所以金世宗時的大臣唐括安禮認(rèn)為‘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④ 到了明代,仍有大量漢人被擄掠成為女真人的奴婢,他們“久居彼境,則語文日變,忘其本語,勢所必然。”① “他們不僅在語言上‘不解漢語’改操女真語,而且在文化習(xí)俗的各方面都逐漸接受女真文化的影響,而女真化了。”② 清代,因東北地區(qū)土地肥沃、特產(chǎn)豐富,大批漢人不斷流入關(guān)外,分散在東北各地居住的漢人因與滿人雜居之多寡成分不同,而呈現(xiàn)出自西向東漢化程度漸弱的趨勢。由于漢人逐年到東北墾荒,至康熙年間已影響八旗生計,尤以京旗最為突出。為解決此問題,乾隆初年施行將京旗閑散移屯東北和對東北全面封禁,尤其對“祖宗發(fā)祥地”實行長期重點封禁,以此限制漢人出關(guān)。為加強“滿化”,封禁措施的第6條規(guī)定“專設(shè)滿官治理州縣”,第7條是“恢復(fù)滿族舊俗”,如滿族官員一律要稱呼滿語姓名,不準(zhǔn)改漢姓呼漢名;山海關(guān)外州縣沒有滿語命名的都要翻改滿語名字;滿人都要學(xué)習(xí)滿語;滿族、蒙古、錫伯、巴爾虎佑領(lǐng)下之女,不許和漢人結(jié)親等。在生活習(xí)俗上,強迫漢人仿照滿族剃發(fā)易服;漢族婦女廢除了纏足;漢人也喜食滿族的食品,如黏食、蘇葉餑餑、薩其瑪、豆面卷子、酸菜、酸湯子等;定親之日,漢人也依照滿族習(xí)俗,女飾盛服用旱煙筒為男家來賓依次裝煙以及兩家主人“換盅”。在游藝上,漢人也學(xué)會玩“嘎拉哈”和“走百病”。在宗教習(xí)俗上,漢人也逐漸接受薩滿教和跳神。總之,在留居?xùn)|北的漢人中,淪為滿族奴婢的漢人(謂“包衣者”)滿化最深,編入八旗中的漢軍旗人滿化也較深,其余的漢人亦有不同程度的滿化。此后,“封禁”、“反封禁”、“馳禁”的斗爭一直持續(xù),直到民國才告終。其影響一方面延緩了東北地區(qū)開發(fā)的進程,另一方面卻也留存了大量滿族文化。民國以后,雖然關(guān)內(nèi)漢人帶來了各種漢文化,但長期封閉的東北地區(qū)因悠久的歷史積淀,仍以滿文化為主,兼融漢文化,似可稱為滿漢文化。
從現(xiàn)存滿族音樂作品中可以看到滿族音樂的特征是:“宮、商、角三音小組是滿族音樂的核心音調(diào),……以采用宮調(diào)式的最多,商調(diào)式、角調(diào)式次之,羽調(diào)式、徵調(diào)式則少見。……由于滿族單詞重音常落在單詞的最后一個音節(jié)上,所以在散板和有板兩類節(jié)拍中,都經(jīng)常出現(xiàn)前短后長或前緊后松的節(jié)奏型,如《三字經(jīng)》式的歌詞使?jié)M族民間音樂中常出現(xiàn)X X X ─‖X X X‖的節(jié)奏型,……由于單詞重音后置,滿族藝人稱為‘老三點’。‘老三點’不但是民歌中常用的節(jié)奏型,也是歌舞曲和器樂曲中最常出現(xiàn)的節(jié)奏型。”① 東北地區(qū)(除滿族聚居地外)能夠體現(xiàn)滿族音樂特征的藝術(shù)形式有東北大鼓、單鼓(旗香、民香)、二人轉(zhuǎn)和部分漢族民歌。
東北大鼓是廣泛流傳在城鄉(xiāng)的說唱藝術(shù)。據(jù)專家考證:“子弟書的興起和傳入,對東北大鼓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據(jù)傳它是在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4年)由子弟書藝人黃甫臣等從北京傳到東北的。最初的演唱形式是演唱者手持三弦邊彈邊唱,腳下綁著‘節(jié)子板’用以敲擊節(jié)拍,老藝人也叫它‘弦子書’。……隨著民間藝人的進城,使原始的、自彈自唱的‘弦子書’形式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女角為主,外加三弦伴奏的演唱形式,這時的滿族大鼓已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② 以上考證表明,“八旗子弟書”對東北大鼓的形成以及早期的東北大鼓曾有過影響。從專家介紹的東北大鼓主要唱腔曲譜資料中還可以看到,“兩大口”是宮調(diào)式;“小口慢板”;“二六折”是徵調(diào)式;“快板”是宮調(diào)式;“散板”、“悲調(diào)”是徵調(diào)式;“扣調(diào)”是商調(diào)式。無論是宮調(diào)式還是徵調(diào)式唱腔(旋律中有變宮)都呈現(xiàn)出以do-re-mi-sol-la為主要旋律音的宮調(diào)式感覺。唱腔旋律質(zhì)樸,無過多裝飾,與唱詞語調(diào)緊密結(jié)合,這些都不同程度體現(xiàn)出滿族音樂的特征。
單鼓音樂(旗香、民香)中的滿族音樂特征和滿族文化特征,已有較多文獻、專著詳細(xì)闡述,其中“旗香”基本是滿族文化的體現(xiàn),而“民香”還沒有全部滿化,如漢民婚娶時不“燒香”,而滿族使之;漢民“燒香”時不用“索羅桿子”;漢民表演時因使用小單皮鼓而設(shè)“小跑鼓”場面;漢民太平鼓音樂的鼓點是兩棒鼓、四棒鼓等偶數(shù)棒,而滿族是三棒鼓、五棒鼓等奇數(shù)棒;漢民只表演“一夕”,內(nèi)容和形式要比滿族少等。①
二人轉(zhuǎn)是具有濃郁滿族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形式,它兼有說唱和歌舞的特點。從諸多對二人轉(zhuǎn)的研究資料表明,二人轉(zhuǎn)融會了秧歌、民歌、什不閑、單鼓等音樂表演形式,② 其中也蘊含著較多的滿族音樂文化特征。早在金代就有“踩高蹺”,③ 它與滿族傳統(tǒng)歌舞“莽式空齊”相結(jié)合,形成其后的“揚烈舞”。這種舞蹈,“舞人騎之竹馬??舞,從此‘揚烈舞’成為清代宮廷演出的重要舞蹈之一。”④“‘什不閑’在乾隆年間曾進入京西八旗子弟倡辦的八旗營之秧歌會。從此經(jīng)過八旗子弟‘雅化’過的‘什不閑’常隨這個秧歌隊于每歲之正月在圓明園的同樂圓演出。……于嘉慶十八年隨北京移居盛京的閑散宗室?guī)е辽蜿枺@時‘什不閑’已成為‘高蹺秧歌’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攜帶方便,取消了‘什不閑’架子,通用秧歌隊的一鑼、一鼓、一鈸伴奏。”⑤ 據(jù)專家考證,二人轉(zhuǎn)的重要曲牌“武嗨嗨”是“文嗨嗨”的變體,而“文嗨嗨”則是流傳于遼寧新賓縣滿族地區(qū)已有120多年歷史的民歌“采花”調(diào)的變體。⑥“據(jù)70多歲的滿族民歌手吳雙浮說,當(dāng)年此歌無名,因為在秧歌隊中演唱,故稱之為秧歌。”⑦此外,金代盛傳“連打廂”,“秧歌的霸王鞭、二人轉(zhuǎn)的彩棒、金錢蓮花落的金錢棍,皆源于此。”⑧
在滿族民歌中,漢族民歌分布較廣,由于滿漢文化交融,使得滿、漢民歌難以分辨。但是從大量的漢族民歌中,依然能找出滿族民歌的痕跡,現(xiàn)僅從《中國民歌》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中所收集的為數(shù)不多的東北三省的漢族民歌中即可窺見一斑。從黑龍江省的《打秋千》(拜泉)、《十根花棍調(diào)》(齊齊哈爾)、《祭腔調(diào)》;吉林省的《小調(diào)》(柳河);遼寧省的《拔白菜調(diào)》(凌源)、《十二月小調(diào)》、《雙五更》(長海)、《泗州調(diào)》(朝陽)等民歌可以看到,這些民歌從節(jié)奏、調(diào)式、骨干調(diào)式音、音腔、旋律性格等方面都顯現(xiàn)出滿族民歌的特征。
綜上所述,滿族音樂在東北地區(qū)的滿漢文化交融中已成為東北大鼓、單鼓、二人轉(zhuǎn)的組成因素,它已由民歌形式進入到說唱、歌舞形態(tài)。如果說,由于受包括滿族在內(nèi)的北方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影響,使北、南方漢族音樂的特點有明顯區(qū)別,那么由于受滿族音樂的影響,東北地區(qū)民間音樂與關(guān)內(nèi)北方民間音樂也有著明顯區(qū)別,其旋律在級進中陡然出現(xiàn)的七度大跳,節(jié)奏短促、棱角分明、音樂性格豪放、潑辣,無不顯現(xiàn)出滿族音樂中“騎射”的文化特征。 在東北滿族人聚居的地區(qū),雖然他們的生產(chǎn)方式和文化教育受漢族影響,但其生活習(xí)俗、飲食、宗教信仰沒有改變,封閉的民族文化圈,深厚的滿文化積淀和民族心理意識,使?jié)M族民歌和薩滿祭祀音樂相對保留其原狀,呈現(xiàn)出原始、古樸的文化特征。
從現(xiàn)存的滿族民歌中可以看到,其內(nèi)容都極貼近生活,質(zhì)樸到直白的程度。如《打獵歌》、《打水歌》、《包餃子》、《外面狗咬誰》、《嫂子丟了一根針》、《小孩睡大覺》等①;其旋律可以感到是沒有經(jīng)過加工的原始民歌,其原因可能是太具有鮮明的原始特征,較難與漢族民歌相融合,且又不具備進化到說唱、戲曲的內(nèi)部因素,所以保留至今。
滿族的薩滿祭祀活動是以家族為單位進行的,他們祭祀的程序和使用的音樂大致相同。從音樂上看,口語化極強,旋律、節(jié)奏起伏變化不大,它與表演、服裝、唱詞、祭器一起呈現(xiàn)出古樸的滿族文化特征。從中感到這種古風(fēng)遺存,與祭祀的嚴(yán)肅、傳承的嚴(yán)格、家族的獨立、封閉不無關(guān)系。
在滿族人聚居地區(qū),滿族音樂還曾發(fā)展成戲曲,清代盛行的“八角鼓戲”和滿族戲“朱春”的產(chǎn)生便是滿族音樂進一步發(fā)展的結(jié)果。據(jù)《滿族戲“朱春”初探》(隋書今)一文闡述,清康、乾時期,在八角鼓說唱基礎(chǔ)上,發(fā)展成多種唱腔、多種曲牌的聯(lián)曲、聯(lián)套曲式,并有場次布景、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故稱“八角鼓戲”。因為此戲產(chǎn)生在北京,故其中也融入部分漢族音樂。大約在同一時期,黑龍江、吉林、承德等滿族地區(qū)又產(chǎn)生了滿族戲“朱春”(“朱春”是滿語,由滿族人稱唱戲藝人為“朱春賽”簡稱而來),它是在祭祀音樂、八角鼓說唱、倒喇(已失傳的滿族說唱)和莽式空齊歌舞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成。以大四弦做主奏樂器,還有笛、大抓鼓、小抓鼓、八角鼓、堂鼓、吊鼓、鐐、鈸、鑼等。其內(nèi)容有對神、祖先的祭祀,如《祭神歌》;有對滿族歷史上重大事件和戰(zhàn)爭的反映,如《胡獨鹿達(dá)汗》;有滿族神話、傳說、故事的內(nèi)容,如《錯立身》(這一類劇目最多,最有特點);還有對漢族戲目的移植,如《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總之,滿族戲“朱春”具有濃郁的滿族文化特點,在滿族地區(qū)盛行一時。其后,此戲種曾一度瀕于失傳。近年來,滿族文藝工作者進行極力搶救,呼和浩特市新城區(qū)的“滿族戲”、吉林扶余縣的“新城戲”、黑龍江寧安縣的“塔戲”、黑龍江黑河市、愛輝縣、孫吳縣的“滿族戲”等都是它們辛勤勞動的結(jié)果,它為人們展現(xiàn)了滿族戲“朱春”的風(fēng)貌。
綜觀滿族音樂發(fā)展的全歷程可以看到,從社會、生產(chǎn)、經(jīng)濟、語言、習(xí)俗等文化氛圍對音樂生成發(fā)展的影響,它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音樂有著共性。然而滿族音樂在特定歷史文化氛圍中,卻有著明顯的特殊性。簡言之,滿族族戲雖然源遠(yuǎn)流長,但是為了生存,在世代不斷與漢文化融合邁入文明社會的同時,形成民族內(nèi)部發(fā)展的極端不平衡。融入漢文化的族民與停留在漁牧文化的族民之間文化形態(tài)有著懸殊差距,由此造成音樂文化發(fā)展的停滯甚至斷裂,使得它不能像蒙古族、藏族、朝鮮族音樂那樣完整又具有鮮明特色的獨立于各民族音樂之中。這種歷史規(guī)定了的特殊性,使?jié)M族音樂在三種不同文化氛圍中生存發(fā)展,從而形成了不同發(fā)展軌跡。雖然如此,滿族音樂卻有著可觀的藝術(shù)價值,并曾影響過中原北方和東北地區(qū)的音樂發(fā)展,給這些音樂增添了無窮魅力,其薩滿祭祀音樂是滿族古代音樂文化的活化石,為世界藝術(shù)家研究薩滿文化提供了寶貴資料。
滿族發(fā)祥于東北,所以在音樂和舞蹈方面,具有強烈的東北地方色彩。其中以民歌小調(diào)賣胡腔最為突出。如:人們所熟知的民歌《月牙五中衫更》,流傳于遼寧的《搖籃曲》、《溜響鞭》等,都是膾灸人做嫌口的滿族民歌。此外在滿族民間還保留有許多禮俗歌曲,如:《滿族哭喪調(diào)》、《旗香祭祀調(diào)》、《薩滿調(diào)》等,均是在各種禮儀活動中必不可少的音樂項目。
滿族民間舞蹈也分另有帶民俗活動和娛樂色彩兩大類,如:《大五魁舞》、《薩滿舞》都是屬于民俗性、宗教性活動的舞蹈;而《大秧歌》、《踩高橋》和《地蹦子》都是純娛樂性的舞蹈。讓人們熟知的舞蹈作品有:流傳于古代的《莽勢空齊》、流傳于沈陽的《盛京建鼓》和后來的舞劇《珍珠湖》等。
滿族分布在中國各地,其中以遼寧省為數(shù)最多,其 次是吉林、黑龍江、河北、北京等地,人口 4299159人 (1982年統(tǒng)計)。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 語支。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漢語漢文。滿族人民原以狩 獵為生,善于騎射,信奉薩滿教。 滿族音樂可分為民間歌曲、歌舞音樂、說唱音樂埋譽 3 類。民間歌曲有 山歌、彎祥段勞動號子、小唱 3種。內(nèi)容有情 歌、勞動歌、婚禮歌、祝壽歌、搖籃歌等。演唱語言上 有用滿語、漢語和滿漢語兼用的 3種。大都為獨唱、齊 唱或一領(lǐng)眾和的形式。宴姿